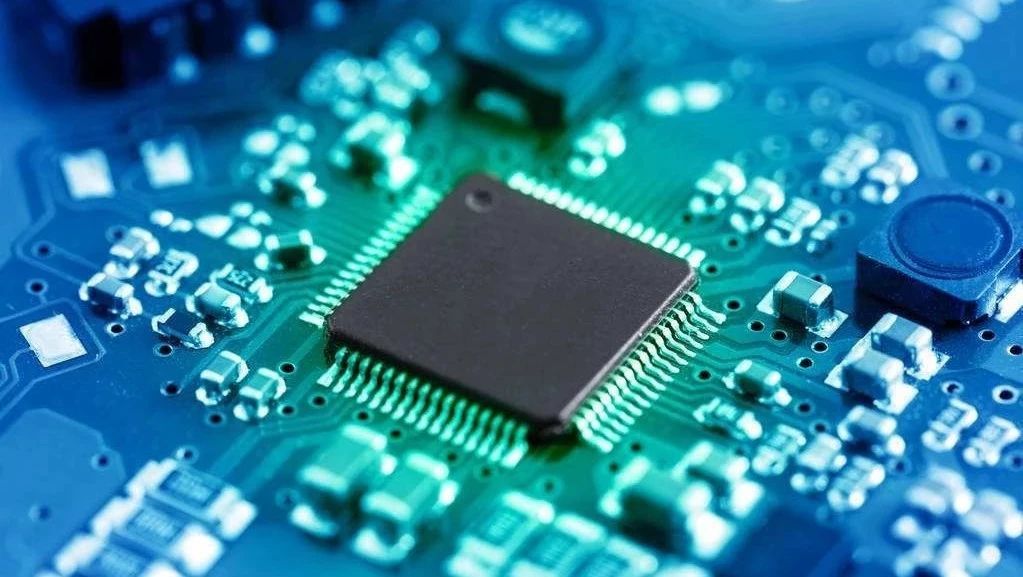
被誉为闪耀在人类科技皇冠上的芯片产业,往往汇聚着一个国家全方位的资源与力量,也放大着千难万难的各路险阻。
今年以来,随着欧盟与美国先后出台芯片法案,世界芯片产业格局风云突变。此时,一个直截了当、无可避免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中国芯片产业,到底如何突围?
近期,网易科技直播栏目《开聊》邀请到北京大学教授、深圳系统芯片设计重点实验室主任何进,芯谋分析师王立夫以及芯智讯创始人兼总编辑杨健共同对话,就中国芯片产业千头万绪抽丝剥茧,直面关键问题,做出关键解答。
以下为《开聊》直播精彩节录:
一、“我们的确是欠账太多了”
主持人:芯片产业为什么如此重要?
何进:芯片是人类技术创新的王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讲,一个是芯片技术的复杂度和精密度。比如,今年下半年,台积电和三星3纳米主流高性能的芯片将量产,而细胞和大分子都有几十个纳米。从这个角度来讲,芯片本身尺度如此之小,但结构如此精密:小小面积上能够集成几百个亿单元器件, 这的确是人类创新的最高杰作。另一方面,今天我们人类刚刚迈进智能时代,芯片技术和芯片产品的应用就像水银泻地一样,无处不在。今天有一句话:“无芯不智”, 无芯更不可能走向智能新时代,科技智能产品没有芯片就不存在,智慧医疗、智慧农业、智慧交通和智慧社区都离不开芯片。从这两个方面来看, 芯片的确对我们非常重要。
王立夫:半导体产业是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对半导体产业有一个简单的定性: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我们芯片产业从设计、制造、封测大概破万亿的规模。全球则是五万五千左右数量级。此外,我们芯片产业增速很快,大概到20%左右。芯片产业对就业拉动有很大作用。先前美国半导体协会和牛津研究院一份报告指出,相比一般科技行业,半导体产业对经济拉动乘数大概是 6.7,而其他统计行业中位数大概是3.7。相当于,半导体行业每雇用一个工人,会间接支撑7个工作岗位。另外,半导体行业还有共富效应。虽然该行业对学历要求很高,但 1/5 左右岗位不需要特别高学历。这就给阶层流动带来了共富效应的机会。
联合主持人杨健:国外某些国家近年来持续对国内有限制,然后再慢慢开始收缩包围圈,可能要限制能够做先进制程的设备,然后又限制EDA工具,还有最新对半导体材料也在限制,所以说是有步骤的、一步一步加码。请两位嘉宾来聊一聊怎么看他们的围堵?然后我们国内的企业该如何调整来突破封锁?在目前情况下,怎么才能更好地做一些创新?说白了就是还没有办法去打破镣铐的时候,怎么带着镣铐起舞?
何进:目前,虽然我们在芯片产业链上设置环节很多,产业链基本建立起来,但在设备和 EDA上受到的影响较大。封装我们已经占了全球超过一半的能力,当然不是最高端的封装。但总的来讲EDA现在受制于人,特别是 14 纳米以下,我们没有一个完整工具可以用。关键设备,一个统计显示国产替代的一个比例至少在 3% 以下。
王立夫:从近几年事件来看,欧美对半导体的重视程度逐渐提升。因此,他们不管采取政治手段,还是联盟战略来孤立我们,这都是未来常态。那我们应该怎么做?作为看市场的人来说,我觉得能做的东西其实很少。包括像刚刚何老师说的先进EDA以及其他设备,可能我们只能突破一种。但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去渐进式做的。我们要有耐心,也要尊重产业的客观规律。
联合主持人杨健:我们芯片产业要实质性提升,应该在哪些领域去做?
王立夫:突围,需要尽人事听天命。在一些关键行业关键细分赛道,我们有一些底牌在手。比如,对美国芯片设计企业而言,他们很大部分营收在中国,高通大概 60 %以上市场是中国手机厂商消化。中国庞大的终端消费市场有非常大的消化潜能,这是我们可以拿来对谈的筹码。
但具体要突破的领域实在太多。现在,中国很多都是点突破。材料这块我们是困难的,比如说先进制程,我们没有那些设备就没办法研发。国外研发都是厂商一起合作,跟着晶圆厂跟着设备厂一起合作研发,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现在,网上一些不良媒体会以我们突破了某一项技术,就认为我们突破了某一类产品做宣传,这是不可取的。
何进:目前从份额来讲,我们芯片产业是两头小一头大。封装表面上看,我们能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但核心的设备还是靠进口。两头小,就是设计和制造份额占得比较低。理想的状况,是三头都均衡发展。
2000年后,我们通过20多年努力整个芯片的产业链已经建立起来了,比较齐全,只是基础薄一点。现在,国家经济大发展,VC 投资也比较多,政府蛮支持创业团队。所以,芯片产业链上每个环节基本上都有人在搞,这是好事。我们国内以深圳为代表的终端市场,无论电脑还是手机产量是全球第一,这样的市场需求也很好。此外,芯片的国产替代品上我们跟随能力比较强,替代步骤在加快。不过,我们设计水平应该算是中上的,设备和材料是中下的。
但总体来看,我们的确是欠账太多了。一个是我们基础研究层面,没有像别人那么多年的积累。第二是我们综合的工业水平跟不上。为什么光刻机造不出来呢?实际上是我们整个的工业水平落后于人,所以才受制于人。此外,现在芯片产业化的确有一些问题。比如,最近几年全国冒出来 2 万多家与芯片相关的企业。其中,跟风造成的浪费以及量产规模问题,造成大量的浪费,一地鸡毛的事很多,有一系列的这个烂尾的工程,我们就不用谈了。
现在,很多项目在讲故事,到处都是挖人,哪里工资高就往哪里跑,所以没有一条线是稳定的,这是很大问题。基于此,我觉得国内现在缺乏统筹的能力,缺乏布局的能力。当然,我始终觉得现在政策是好的,我们有钱大胆的投资也是好的。
二、“中国自己被抄了作业,是不是也证明被外部的认同了?”
主持人:为什么现在这么被动?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何进:在正常产业分工下,比如中芯国际现在 14 纳米如能生产,两年可以完成产能爬坡。但我们要到7纳米、5纳米一直到 3 纳米,正常来讲应该要8 年到 10 年时间。但是目前情况是产业分工不正常,政治地缘代替了效率更高的正常产业分工,可能时间会更远一点。
王立夫:关键是设备这块被限制。业内有个段子。零几年时候,中芯国际能到世界第三。近几年则倒退到世界第五左右。可以说,不是我们没有前进,我们成长也很快,但奈何对手跑得更快。因为在产业链以及话语权获取资源的能力上,他们高于我们,体系建设也相对完善有先发优势,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实际问题。
举个例子,现在国外材料厂商卖给中国厂商的产品,基本会以高于国外厂商 50% 价格出售。那设备厂商加价的现象,就更严重了。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厂商体量就小,更重要的原因是,从领先技术的研发合作关系上说,国外厂商之间生态的的深度合作才是他们共同快速成长的关键所在。
主持人:人家跑得比咱们还快,那咱们怎么去追赶呢?
何进:我觉得目前来讲没有什么捷径的路可以走,唯一的可能就是在人才培养上多助攻。所谓人才,分两个层面:一方面我们要大量培养人才,在量的基础上去想出一些培养创新天才的主意和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真的要以更大力度来引进海外人才:不管是海外留学,其他国家,还是说台湾同胞。我插一句题外话,今天无论是台积电还是 GPU 龙头英伟达,华人在芯片行业的老前辈,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华人在芯片领域从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脑子。
因此,如何让人才为我们所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我觉得,这是政府层面需要考虑的。2020年前,我曾经在深圳,北京和青岛等地多次举办高端的芯片论坛活动,邀请国际上知名的蒋尚义博士、马佐平院士等海外华人芯片专家回国做讲座或交流,曾经一段时间他们很容易来到大地方陆。但可惜我们当时没有很好的保护他们,利用他们的建议和智慧,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目前这个情况下,我们破局的手段除了有钱,怎么好把人才利用好、怎么吸引人才是很关键的。
王立夫:在产业政策上,如果想追赶欧美日韩的企业,还是有措施可做。首先,我们有着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像过去我们采用了大基金形式去市场化运作。现在,欧美反过头来选择了抛弃市场化、采用政策补贴的举国体制,去抄中国的作业,去强化自己。我有时候经常思考,中国自己被抄了作业是不是也证明被外部的认同了呢?因此,回顾中国整个顶层设计,我们可能需要在未来再出更多更深的规划,来加强统筹芯片全局的能力。
第二,就是说刚刚几位老师提到的话语权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经常服务地方政府常遇到的问题。像南方地方政府,因为产业发展得比较好,他们对产业认识,包括领导班子长期对投资和学习积淀是比较深的。但像像一些内陆城市其实还是欠缺的。所以有必要从政策的方面去成立一些产业小组,以企业家、学者、产业人士,去建立一些常态化运行机制。
第三,对于一些特殊性质的企业,对产业发展有关键带动性、平台性、扶持性作用的企业,除了面上的这些政策,应该还是要进行点对点式的支持。此外,还是避免运动式的政策,也要避免领导换届出现的政策不可持续性。
而从这个产业层面上,我觉得像包括何老师之前提到的通过组织外籍专家、行业专家、企业专家、产业专家,去形成顾问委员会的形式,去给我们的企业和政府进行梳理。比如,从这个时间上来说,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可能长期需要耐心等待的,哪些是我们短期可攻克的。国际层面上来说,要分清楚哪些是我们需要跟国际企业去合作的,哪些是我们要完全自主的。从这个市场的属性说,要分清楚哪些是可以通过市场化解决的,哪些是必须要通过政策性导向或者说特殊手段去解决的。
三、“我相信,中国甚至比美国还能做得更好。”
联合主持人杨健:这个行业领军企业的高管里,有很多华人,而且国内很多科创板上市的公司,也有很多美籍华人,所以说这个行业的高层次人才是有非常多的华人。但是反过来看,在高层次人才这块,本土的半导体高层次人才其实还是很缺失的。所以,如何吸引海外的人才回来,是要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怎样去培养本土具有创新性思维的高层次人才,那同样又是回归到国内的教育环境,或者是各方面的策略,可能就是问题关键的症结所在了,两位怎么看芯片领域人才稀缺和人才培养的问题?
何进:我在美国和中国大学都待过,对我们目前机制说两点。第一,我们科研项目,特别是芯片类科技项目,对人才培养的经费投入比例和国外有很大区别。美国科技项目培养多少个硕士生和博士生,这是它硬性指标。因此,他们把70%钱花在人上,这是非常关键的。而我们国内过去项目70%钱是买设备、关键材料。过去,我们在人的花费上硬性规定不能超过15%,这是一个大的问题。
第二,是国内出原创思想和概念的地方和国外有很大区别。国内的框架下,对项目考评机制是跟国外不一样的。其次,我们的产学研和国外有很大区别。比如,美国在芯片行业里面,虽然他们现在芯片法案要建几个全美研发中心以及国家基金,但美国这些教授的真正项目,来自于一个比较特殊的组织:SRC ,就是半导体研发公司。
这公司是个基金公司,而不是一个研究的公司。他类似我们的大基金,但公司的钱不是来自于国家,而是英特尔,AMD, TI 等国际芯片巨头。拿钱后,公司就会发布指南,发布下一步芯片科研创新的一些题目; 然后让教授去申请,公司再来支持,这是主要的一类,叫CORE PROJECT。 还有一类,就是以用户来定义的形式:如果方案好,有2-3家公司直接支持,教授团队就能够拿到项目并完成, 这一类项目叫 CUSTOM PROJECT。并且,SRC项目申请方案不像我们国内申请一个项目少不了几十页说明,他们就两三页纸。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申请过这类项目,一般不会超过三页纸。
此外,项目的研发过程中,会培养相应的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学生假期会去出资的企业做实习,带着研发的成果去实现、去试用、再去改进。此外,SRC公司组成了一些专家评审团,每个项目至少有两个公司的专家指导项目的进展。并按照时间节点,审核一年的业务效果:好的继续,不好的拿掉。
因此,现在国内的产学研之所以做得不好,除了经费分配有问题,项目考评的机制有些问题。
今天,我们中国仅科创版就有很多芯片上市公司,他们目前没有特别缺钱。因此,是不是也可以组成美国SRC这种类似公司,来支持研发一些关键技术甚至共性的芯片技术?
公司如果出了钱,技术层面、人才层面就会有回报。如果不从这些方面着手,要学校无偿培养人才,我觉得老师没有这样的义务,其次,学生跟你的产业结合也不紧密。否则,学产研就成了几张皮,是做不好的。
主持人:我们应该怎么去调整?
何进:我们国内过去没有钱。但现在,产业界包括华为、中兴通讯、中芯国际等公司为什么不可以组建这一类的这种SRC联盟?把我们产品线的创新研发真正挪到学校。当然,这需要各级政府去引导,各方共同出钱。我相信,中国甚至比美国还能做得更好。
王立夫:从生态搭建上来说,中国芯片厂商还需要做更多工作。为什么美国EDA工具应用那么广泛,或者说,他们这些器件为什么得到那么多工程师应用?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预备工程师这个群体聚焦非常准。从他们接受教育开始,使用的就是这个某些特定厂商的产品,那到了这群人工作就会形成思维定势,对这种产品熟悉度、粘性会好。就像我们说从娃娃抓起,从大学生开始抓起。而这一块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他们这块的生态确实不错。现在,中国的芯片厂商最近也朝这块努力,会跟学校联合。不过,成效还需要耐心等待。
四、“回归正常的时代之前,我们需要修炼好内功。”
联合主持人杨健:未来,对抗会是常态吗?
何进:现在,国外戏剧化的政治人物频频上台。现在的逆球化是不正常的时代,浪费了人类的资源和时间。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加强我们的基础研究,这个层面国家确实在不停的投入。其次,我们要真正实现有效的产业化,产学研的机制真的要把它改进起来。
正因如此,我们要打好基础,等待世界之变。我觉得世界不会一直这样下去,这是不可持续的,人类最终还是理智的智能生物,不会一直昏下去,有理性的声音,最终光辉就会照耀,最终回到理智的轨道上。在此之前,我们要练好内功。
王立夫:从历史的角度上来说,对抗其实发生过很多次。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英国当时限制这个美国技术外流,水利设备机器、图纸设备零部件不让流向美国,人才包括工人都不允许往美国输送。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但结果怎样呢?当年英对美一系列封锁过后,美国却在工业革命后成为了工业霸主。
因此,我个人对现在产业既担忧又高兴。先前,我有一次出差跟一个出租车师傅聊天,他就开始跟我聊高科技。当时我是真的很诧异。现在,全民科技意识逐渐觉醒,这很重要。
但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还是要理性、客观、耐心地看待芯片产业,尊重产业的发展规律。而作为一个从业者,我觉得这个时代:可谓时也运也。这是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责任,也是我们身处这个时代的使命。或许,美国采取了一种阳谋的措施来消耗我们,那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拿出自己中国人的骨气和自信来去把芯片的功夫去做实做深,只能硬着头皮上。这也是现在面临的一场很大的危机,但危机危机,危中有机。
我相信市场不会一直封闭。事实上,中国不是真的想自己把所有产业都搞完,想的还是合作共赢,更符合全人类分配利益和效率的境界。正因如此,我们既不要对高科技盲目狂热也不要过于悲观,这还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哪怕现在不大正常的时代,但全球分工还是回来的,我觉得我们能看得见。









